导语:最近几年,社会上屡屡出现女性在公共区域被侵犯的新闻,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索女性本身、女性与社会、女性与男性之间的问题。女性在人类千百年的“父权制”社会里,都是弱势群体。
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女性自身主体意识开始增强,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身心,女性团体开始为平等而做出种种抗争,女性在各方面逐渐取得了与男性相对等的利益与地位。
李小江教授在最近新出版的《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女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改革开放之后,都市的女性地位更是高于农村的男性。现在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问题,或许因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同构,在深化性别的社会差异方面形成了共谋。李教授反对“女性主义”开创者波伏娃对女性所做的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是天生的,非是后天被人为造成的。我们要尊重女人的天性,不能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将男女一概而论。“女性解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它仍旧在路上……
嘉宾介绍:李小江,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妇女文化博物馆荣誉馆长。曾为郑州大学、大连大学教授。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性别与中国”、“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等。主要著作《夏娃的探索》、《性沟》、《女性审美意识坛微》《走向女人》、《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导读》、《女人:跨文化对话》等。
采编:宋晨希 特别鸣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小江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何急于颁布《婚姻法》?
搜狐文化:李教授您好,您作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女性学研究开创者之一,其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典范意义不可忽略。首先,想从您的个人经历出发,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女性主义研究这条路的?是什么原因,激发了您的女性自我意识?您这么多年的研究,又对中国的现实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小江:首先要解释,1980年代我们开始做妇女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研究。我们的社会主张“男女都一样”因而在主体意义上抹杀了“女性”,我们的起点因此是“走向女人”(我的一本书名)而不是简单地争取男女平等。生在新中国,激发女性意识觉醒的并不是歧视性的社会观念,而是女人自己力求“都一样”的生命实践。
男女原本就不一样嘛,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和男人一样呢?理论上说的是一样,实际评价标准却不一样,双重标准成为双重压力,让我们无所适从。没有哪个男人能够给女人指明“正确”的方向。女人要想走出困境,只有自己去找答案,我们的妇女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
30多年过去,要说影响,不是一家言论有什么开天辟地的作用,而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学术作为,让中国的女性研究能以独立自主的形象自立于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归纳起来,大体在四个方面:其一,通过不同形式的女性教育,召唤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中国历史上,这是女人第一次在精神上摆脱民族国家的纠缠(如秋瑾等)、走出家庭的庇护和男人的指导(如五四运动),自己发起、自己成立组织、自我意识全面觉醒的一个新起点。其二,集结学术队伍,在学界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奠基工程。“妇女研究丛书”的出版(1987-1991)、“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启动和拓展(1992年至今)、妇女文化博物馆的创建(1992年至今)以及女性/性别研究在高校开课等等,既是例证,也是见证。其三,比较西方女权运动,我们的妇女研究从开始就立足本土,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而不是女权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没有落入第三世界妇女研究的困境,在缓解后殖民主义的侵蚀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四,与我个人的研究有关。自始至今,我的研究没有局限在“女性”的小圈子内,没有停留在任何“主义”的单一框架里,视野和方法都是越界的:在世界史进程中做跨文化比较,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做文化阐释,让思维从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回归地缘人类学——我以为,这个影响是长远的,借助女性和性别研究的微观视角,完善人类自我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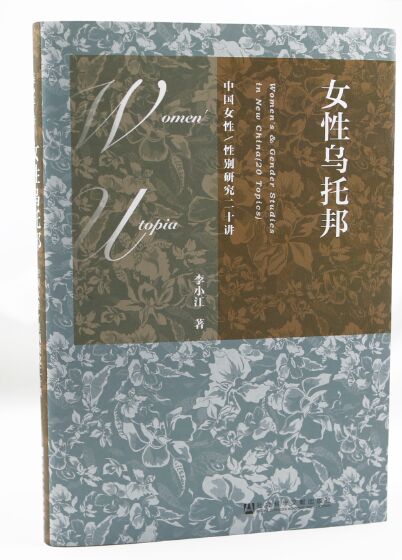
《女性乌托邦》
搜狐文化:在您新出版的这本《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里面,曾对新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给了很高的评价。的确,1950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就颁布了《婚姻法》,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为何会那么急于颁布《婚姻法》呢?
李小江:《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大法,就客观效果看,它的确是一部解放妇女的法;但它的出台并不直接出自解放妇女的目的,而是为了稳定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社会秩序。政权更迭,泥腿子进城,顷刻间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在外是接管权力,在内是安家——中共历史上,“家”的问题终于浮出地面,成为建国安邦的前提,为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中共高层干部曾经都是离家出走的,老家有原配妻子,参加革命后又有了新的伴侣,新旧碰头,怎么办?制度性的规范首当其冲。可见,无论什么时代,婚姻家庭及和谐的两性关系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上世纪50年代颁布《婚姻法》之后连环画上的自由婚姻
搜狐文化:西方的左派和女性主义者对中国建国之后女性所获得的至高地位极度吹捧,认为中国给世界女性解放带来了范例。但当时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铁娘子”的口号,忽视了女性自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受到很多人的诟病。您长期以来,做女性口述史研究,很多女性如何看待那段日子的“平等”?
李小江:从社会层面看,“半边天”的历史意义值得肯定。有代价,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个体生命中,极端的言行造成一些悲剧性的女性人生。即便如此,妇女解放的基本性质不容否定,这与我们在口述采访中获得的信息是一致的:不管有多少困难和坎坷,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解放初期的女性(五类分子家庭的除外)对“解放”众口一词给予高度评价。当时,阶级问题的压力远在性别之上。
妇联在改革开放之后托住了生存状态恶化的底线
搜狐文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您在书中也提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里的女性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中国女性地位自解放之后到今天是处在下降地位的,现在女性地位越来越低,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有些人提倡传统,让妇女回家,工厂、公司甚至开始排斥用女性员工等等,以及找好工作不如嫁对人的理念,这是否是父权社会继续发挥了作用?
李小江:“地位”与“压力”不是一个概念。今天的社会,从立法层面看,女性地位不低;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空间看,女性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自己的感觉不佳,内外交困,生活压力空前沉重。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认识没有跟上,因此会有“下降”的错觉。旧的观念抬头,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别制度发生了本质性的倒退。
“父权”这个词说在今天不那么有说服力。你去问问那些男人那些父亲,他们其实还有多少特权?他们还有哪些权利或利益是通过剥夺或禁锢女性而获得的?如果不是,就要寻找新的原因。在我看,全球资本化是一个主要原因,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曾经是同构的,在深化性别的社会差异方面是共谋。
搜狐文化:与西方的女性团体相比,中国的女性团体似乎一直处在缺位和失语的状态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我曾经读到一本书《美国人为什么恨政治》(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著) ,里面提到美国女性可以为了种族歧视甚至反堕胎运动上街游行抗议,他们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女性自“文革”之后,这种团体性的反抗就没有了,各自为政。甚至,就像您说的,现在中国女性自身主体意识是欠缺的?您认为,这是怎么造成的?妇联或者说女性团体应该做一些什么?
李小江:这种说法我不同意。就说新中国吧,中国女性团体不仅没有缺位,而且非常强势。全国妇联这样的机构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妇联组织不是一个虚设的花瓶,1950年代在解放妇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改革以后托住了妇女生存状态恶化的底线。
1980年代,民间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布中国大陆,发出了女性自醒的声音,怎么能说是失语呢?失语的问题出现在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西方女性主义坦然登陆,全面占领了主流话语平台,女界学界盲目追风,一时迷失了方向。怎么办?没关系,回头寻根就是了。只有见过世面,领教过世间风雨,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最该珍惜的。

1995年,北京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人民大会堂举办欢迎仪式,和平鸽象征了本次会议“平等 发展 和平”的主题
女人被塑造成“第二性”非男人主导 而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阶段
搜狐文化:西方的权力理论、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现在全球最时兴的三套理论,前两种现在中国学界也大谈特谈,但唯独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一直不声不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使学者做这方面研究,也多是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或者历史,现实方面几乎没有人在做。您作为一个学人,为什么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得不到重视?
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很多章节都涉及女性主义,从不同方面讲述和分析了它的来龙去脉、历史命运和学术作为。1995年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社会活动家借世界妇女大会的契机进入大陆,从根底里改变了中国妇女的话语结构。不信你去看看这些年的主流报刊,到处都是“社会性别”。什么是“社会性别”?就是gender,新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与自然性别划清界限;再去看看学术论文,但凡涉及女性的,无不以女性主义为基本方法。如此作为,20多年了,女性主义独占鳌头,没有经过必要的理论清理,拿来主义,这不是什么好势头。
搜狐文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纷繁,比如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等多达十几种,但有一个倾向就是认为“女性(sex/gender)是被生造出来的词,比如巴特勒就持这种观点,女性是后天培养而成的。但是,从波伏娃开始,很多女性主义者比较注重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性,认为这是她们不同于男性的一点。所以,您如何看待说女性是生被造出来的这一种说法?又如何看待女性在力量、身体方面的劣势?
李小江:这里可能有误解。“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恰恰是波伏娃的名句,在《第二性》中出台,成为新女权运动的引路圭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同她的说法。我在《女性乌托邦》代跋中谈到了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对“自然”和“历史”的态度。在我看,女人(women)的确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我不认为女人被塑造成“第二性”全然是男人主导的社会结果,宁可看它是人类历史进化中一个必然的阶段。在我这里,“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搜狐文化:现在虽然可以看到民间有很多团体倡导女性意识,但是,仔细看他们倡导的内容,很多都是关于女性如何相夫教子,做一个好的家庭主妇等等,让女性回归家庭,或者如何让女性保持魅力,不让男人在外面找小三。这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李小江:我会说这是传统的性别意识作祟,而不会轻易使用“歧视”这个概念。“歧视”隐含着一种先验认可的等级意识,不加区别地用在今天的女人身上,不合适。走遍世界看看,今天的女人,有弱势的,也有强势的,更多的是不受歧视能够自食其力的。今天说“回归家庭”,有怀旧的,有给社会开药方的,鱼龙混杂,未必都是倒退,有些就是女性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搜狐文化:自从尼采、福柯以来,很多西方哲学家开始注重“身体”。福柯在《性经验史》里强调,身体如何在现代社会被规训。其实,女性身体一直是被父权社会消费的过程。现在,广告、电影、艺术等等媒体都是以女性身体作为看点,很多女性也在这其中不知不觉形成了共谋。比如,女性会故意穿着暴露,故意借此机会吸引眼球等等。这是不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崩毁?您如何看现在这种现象?又如何去改变?
李小江: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消费”。这是一个资本概念,与市场行为有关。它原本是中性的,被左翼学者在话语重构后成为一个负面词汇。我不赞同用“消费”或“被消费”这样的对应概念解释社会现象或从事文化批评。身体与衣食住行直接关联,消费是常态;被消费则可能有多种走向,比如劳动,出卖体力,被消费是正常的;卖淫,出卖性色,似乎就不那么正常。
市场经济讲究公开和公正。身在男女共处的现代社会里,女人和男人一样,捆绑在资本运作的流水线上,有消费才有生活,被消费也意味着价值的社会认可。这都是诱惑,对农业社会的道德观念是颠覆性的挑战。谁是谁非呢?不着急,风水轮流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玩转了各种价值,唯独在商业和金钱面前不那么坦然从容,还要几个筋斗才能翻出试错的泥沼。无论什么时代,主流社会价值观说起来都是劝人向善的。是否能够从善,要看你自己,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必事事与时俱进。

法国哲学家让-波德里亚,对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作了开拓性的理论剖析。
搜狐文化:现在还有人强调嫖娼合法化(这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合法)?您怎么看待这两个问题?西方女性主义者如何看待嫖娼问题?
李小江:“嫖娼”这种说法本身有问题,是从男性角度定位的。海外许多地方更多地把这种事看作单纯的市场交易,没有附加那么多的道德判断。性需求是合人性的。单一性别集中的地方(如军营、建筑工地、矿区等),性别比例不平衡,有性的缺失就会有性的市场,与个人好恶没有关系。西方一些女权主义者用“性工作者”取代“妓女”,为自主自愿的性交易去无污名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